出埃及记

果真还是无产阶级更难对付一些
Summary
经历了折腾不已的反复检测、徒有其表的酒店隔离,拿到健康码的人,终于可以前往机场,登上飞往祖国的班机。
来到安检处,搬运工招呼我靠近,俯身把一件行李搬到传送带上。我也赶紧把剩余的行李自己搬了上去。趁着俯仰的间隙,他低声说:“小费、小费”,边说边用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再胸前做数钱状。
我忍俊不禁:其实他普通话发音比广东朋友还好,手势大可不必。
我说:“没有”
他一脸不快地盯着我:“小费。”
我笑着说了声谢谢,径直向安检门走去。
他只是机场雇佣的杂工,也不敢过于纠缠,后面还有很多乘客等着过安检。 我想,总有许多人会比我善良。 得了别人帮助,多少给人家一点钱表示感谢,本是合情合理之事。但很多时候,这变成了“欲从此路过,留下买路钱”式的要挟,要迎合这种要挟,如此善良,我不乐意。 安检门处的安保员例行公事般用双手在我身上从上往下一扫,便让我过了。 安检门左侧,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靠在椅子上,双腿呈八字形打开,一脸认真地盯着面前的屏幕。 果然,我才把行李从传送带上提下,大光头便指着其中一个大纸箱说:“拿过来,打开”。 我把纸箱推到他脚边,我的旁边,在我后面过安检的一位小伙子,也接到同样的指令,迅速打开了他的旅行箱。 大光头让小伙子从箱子里取出一个白色的盒子,至于我,则让我划开塞满杂物的纸箱,翻了一下,让我把几盒护肤品取出。 少不经事地小伙子紧张地问我:“大哥,你给他们说一下,这只是化妆品啊!” 我笑了:“没事,是什么东西不要紧,他们只是要钱而已。我不想给,大不了我就把东西留这儿。你要想给,给一点就行。” 然后我转而跟大光头理论。 我带的那几盒护肤品,是两年前妻子带来埃及的精华液。当时预计在埃及至少呆两年,带的就有点多,结果去年疫情突发,一家人回国,很多东西便留在了埃及。 后来考虑到儿子也到上学的年纪,索性就在国内上学,妻子当然不再来,这次回国,我把她还要的衣物用品一并带回。那个纸箱里装的便是。 我跟大光头说:“这不是埃及产的,是我之前从中国带来的,这里都是我家人的东西”,我顺手从纸箱里拿起儿子的小拖鞋在他面前晃了晃。 他打开盒子,拿出一小瓶看了看,又拿给他上司看看,询问怎么处理。 上司就站在我面前,我同时向他俩说明:1、这是中国产的护肤品,不是埃及的东西,也不是违禁品;2、我是学生,不是生意人;3、你们要硬说这有问题,大不了我不要了。 说完第三点,我把那盒精华液放在了他们桌上。 我看着上司,他一言不发,脸上带着明镜高悬式的迷人微笑,仿佛在说:“不好意思,这是我们的工作,我们是有原则的。” 大光头也有些犹豫,询问上司怎么办,上司不置可否,口中说的:“这是中国产的”,眼睛里却说:“自己酌情处理。” “大哥,我给他钱他不要啊”,此时,小伙子举着他打开的皮夹,一脸无辜地向我求助。 我又乐了:“你这么明目张胆地给,他肯定不要啊。要给得隐蔽点!” 此时,大光头示意我把另外两个箱子也拖过来。 我拖了过来,心想:要找什么麻烦随你便。 他身子朝我倾斜一些,指着那几盒精华液,悄声说:“把它们分到其他其他箱子里,快”,边说边用手示意让我弄完快走。 言下之意是:本来是不许带的,我做个人情,私自放你一马,你把它们分散,每个箱子里放一点,就不会很显眼,我也好交差。 我说:“好”,又给他和上司说了声谢谢,把东西放回纸箱,合起盖子,把行李搬上推车,继续朝着前方走去。 暂停了一会儿的安检工作又重新开始,下一位中国旅客又穿过安检门,行李又提到大光头面前。 一路上,我陆续听到已经出来的人谈论着刚刚经历的安检,有人给出了仅剩的两百埃磅,有人被索要一百美金,讨价还价之后,不知道最后给了多少。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,展示现代化的屠宰设备:白白的肉鸡们,双脚固定地倒吊在传送带上,依次通过一个飞速旋转的刀片。刀片的位置,刚好齐它们的脖子,一只送到,“刷”一声便断了气,接着是一下一只,如此源源不断。 我推着小车继续前行,身后似乎便是这样一架庞大机器,暂停了一会儿,现在又从新开动起来,并将日复一日地运转下去。 它几乎专为中国人设计,犹如那架屠宰器,专门用来咔嚓肉鸡。
我的中国同胞们,喜欢并擅长用钱解决问题。 别人也不傻,摸清了中国人的习惯,也都擅长针对中国人制造问题。许多事情,一旦是中国人,便多半会被或公然或暗示地索要“小费”,法制越不健全的地方,这种现象越是普遍和严重。 这是观念塑造现实的极佳例证。 埃及机场的宰客之风,据说是被人肉带货的朋友们培养起来的,为了使自己超量或违规的行李顺利通关,一进机场,他们便把钞票当作通行证,一路畅通无阻。 这大约也是现实。 但把罪责全归到他们身上,却又言过其实。 任何一个系统要稳定运作,需要其中各个要素的密切配合,就像那架屠宰器能顺利运作,除了感谢设计者、感谢机器,还得感谢鸡:它们个头都一般大小,动作高度一致——一动不动,不管是被宰的还是待宰的,都情绪稳定、鸡极配合。 如果其中有一只鸡试图挣扎,其他的鸡便会嘲笑说:“有什么用?” 所以,有时一个人旅行倒是好事,省心。比如这过安检的事,如果不幸遇上一个“聪明”的同伴,他大概会善意提醒:“算了,给他吧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 而我说不定会被他说动,掏钱了事。生活中的许多“善意”,往往就这样杀人于无形,不断拉低我们的行为标准。 很多时候,我不太明白所谓的“有用”是什么意思。 是说一件事的结果尽如人意吗?如果结果十全十美真的如此重要,那长远来看,我们的结果都是一命呜呼,如果不论后世之清算,只以“有什么用”的思路来看,横竖都是要死,为何还要用心而尽力地生活? 人总是渴望意义的,即便他嘴里常说意义又不能当饭吃。 哪怕明知没有用,还是得挣扎一下。因为在无能为力的处境里,这一点点挣扎,是我们之所以为人仅有的证据。否则我们和那些引颈就戮的肉鸡有何区别? 在现代社会,面对强权,大多数情况下,非暴力不合作是弱势一方最佳的、也是仅有的武器。 生命的尊严如同弹簧,压迫有多大,反抗便有多强。如果是以生死相逼,自然会以命相拼。 幸而现代社会终究是有些进步的,大多数时候,我们要捍卫的权利,尚不至于必须抛头颅洒热血。不必舍身就义,但合理表达自身的诉求是应该的,必须告诉它:这不合理、不合法、我不愿意。 哪怕结果依旧不能如我们所愿。 如果硬要问有什么用,我想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用吧。
首先,强权的运行也需要成本,如果要捏的柿子很多,它一定先捡着软的捏。你不完全配合,稍微硬那么一点点,它必定先把你放一放,先去捏其他。有时,说不定你能耗到他手酸无力之时,所要保全者有幸得以保全。 至少,因为可捏的柿子太多,每次都拒绝给钱的我,最后都还是顺利成行。 当然,其他的事情上,这样的运气未必常有。如果捏柿子是一项有意识的系统性工程,那不管硬的软的,多半都是要捏碎的。 可那些软得过分,才听说要捏,就自行变成果酱的,显然将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人家的短期计划,本只是捏柿子,见柿子这么软,怎能不动其他心思?于是进一步把你果园里的李子、桃子、橘子一并捏成惨不忍睹的果酱,岂不快哉! 第二,越多的配合,会使强权越肆无忌惮。每一次,当我们平静地表达:“这不合法、不合理”时,都在同时提醒侵害者和受害者:我们共同见证的这一切本不应如此。之后,侵害会如期发生,但至少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一种侵害。 我相信,我每次过安检,之所以都有幸能全身而退,必定是因为一直以来,也时常有人对他们说不,因而大光头们还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不合理不合法,所以才不会将我的拒绝视为挑衅。 反之,如果受害人一言不发,甚至积极配合,一旦所有人都如此应对,受害者便成了侵害者的共谋,一道将整个社会的观念水平推落悬崖;一旦沉默和配合变成常态,常识从公共生活中退场,原本再正常不过的行为,便会被视为对权威的挑衅和威胁。 领导讲话时,听众鼓不鼓掌,本是及其自然之事。 但在常识丧失的情况下,不鼓掌会变成要命的罪行。 《古拉格群岛》里写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,其中有一段,写到某个区的党代会通过了致斯大林同志的效忠信,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鼓掌,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时间似乎流逝得越来越慢,人们开始手掌发疼、手臂发麻,年纪大的人逐渐体力不支,可是没有人敢停下来,必须使劲鼓掌。 终于,十多分钟后,造纸厂厂长撑不住,停了下来,所有人都得救了,也跟着停了下来。 当天深夜,厂长被捕,罪名很多,当然,其中没有“不鼓掌”一项。 在鼓掌已经变成罪行的时候,敲着键盘号召别人“不鼓掌”,这过于卑鄙的,我不屑为之。我的意思是,在“不鼓掌”还没有变成罪行的时候,我们能不能别那么使劲鼓掌?能不能稍微“不配合”一点,别台上的人打了个嗝,台下的我们就掌声雷动?至少,这可以让不鼓掌有罪的日子来得晚一些。
我压根不是什么勇敢的人。 我想,过安检时,如果不给钱我就没法登机,或者就要把我弄到小黑屋里关上几天,我多半还是会乖乖给钱。但既然没到那份上,大不了他说什么违规,我就把什么留下,这点损失,尚在可承受的范围内,那为何不争他一争? 无论什么事,争取过了,尽力而为了,结果如何,也就不重要了。人力所不及之事,主不责成。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,凡事才一开始,我便会做最糟的心理准备。我们面前有两条路,一条是死路,另一条也是死路。很多争取,我相信终将以失败而告终。 可死路和死路不尽相同,失败与失败别如天渊。 同为失败者,有人必定要嘲笑:“你看,还不是一样”,但我对那些业已尽力的失败者始终满怀敬重。 究天人之际,人力已尽而不可逆者,天也。即是定然如此,便无怨言。 而之前,凡事还得尽力而为,就像终会成功一般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又完全是一个乐观主义者。 终究,天卷地裂,万物归寂,能随我们抵达主之御前者,唯此心而已。 它还好着,一切便都好了。
我有一件破旧的长衫。 这件褐色长衫来自南亚,料子不错,透气,穿了很多年,胸与背的部分,经常被汗水浸渍,再怎么洗,颜色都更深一些。屁股和膝盖的部分,也因常年磨损而稍显稀薄。 今年的旅程,折腾人的事多一些,便没工夫考虑着装。但之前几年,每次要归国,去机场前我就换上这件长衫,踩上一双旧拖鞋。 中国人相对还是讲究穿着仪态的,一般就东南亚的兄弟们会如我这般打扮,而且,同样是长衫,人家一般也没我这么破旧邋遢。 如此,我站在一众仪表堂堂的同胞之间,自然鸡立鹤群。 来到安检处,照样奉上我的三段论:1、没违禁品;2、不是生意人,没钱;3、硬说有问题你就把它留下。 这一身打扮,把一个“穷”字写满我全身上下: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。 前年归国,又是同样的场景,负责安检的两位在我箱子里翻找了一下,无非是些衣物、书籍、巧克力之类,便挥手示意:走吧走吧。 合上箱子的瞬间,只听其中一个对他的同事说:“哈扎米斯基呢(这是个穷光蛋)” 我一转身,就火速滚得远远的,边滚边笑,差点前仰后合。时过境迁,即便如今讲起,依旧觉得十分好笑。
果真还是无产阶级更难对付一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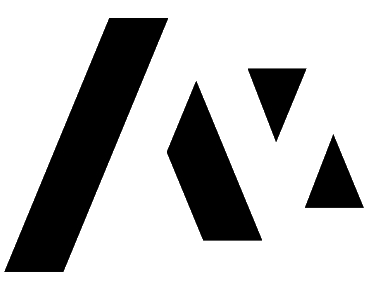


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