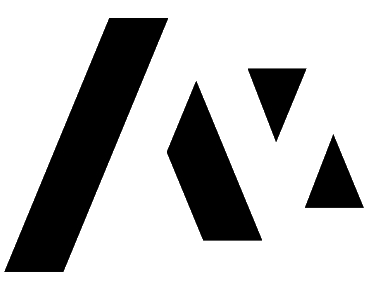其实,罪恶本身,并不能在仆民与真主之间产生阻隔,也决不会减损真主的慈恩与饶恕。
我们可以将伊斯兰比作一棵树,一棵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的树。
有许多的年轻人,在热忱的寻找将虔诚植入内心的方式。
根据先贤那里传来的内容,我们的先知是一个长期思索、大量赞念、多愁善感的人。
望见清真寺亮起的灯盏,徐徐升起的日出,新的一天来了。
你好,传说中的三月一日。
鲁迅先生说,如果你不能握起拳头,至少你可以竖起中指。
对于娱乐圈的八卦,我一向无甚兴趣,但此番瓜熟落地,力宏势沉,砸出深坑。在朋友圈的一惊一乍中,我居然也知道了大概的来龙去脉。
顺便也看到很多朋友或戏说或正说,表达着他们的对婚姻的看法。
有人在问:“恐婚怎么办?”
好像还真没什么办法,这种恐惧自有其来,其合理性深深根植在如今的社会中。
十多年前,我决定不再把自己的私人生活放进文字里,因为突然意识到人与人之是如此不同,也意识到自己是如此贫乏,个人那些苍白的经验,对于他人实在无甚助益。
不料事到如今,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记述一己的鸡零狗碎,实在是表达空间日渐收窄所迫。
风声雨声读书声,最好你别吭声,家事国事天下事,一切关你屁事。
这是和谐社会的需要。
但说说自己,总还是可以的吧——至少目前还可以。
当妙手著文章的理想碰上篇篇404的现实,讲故事便成了最后的渠道。等哪一天真实的故事也不能讲,就只好编童话、神话和鬼话。
人活着,总是要些话的。
经历了折腾不已的反复检测、徒有其表的酒店隔离,拿到健康码的人,终于可以前往机场,登上飞往祖国的班机。
朋友圈的好处之一,在于它在同一时刻,为我们呈现着不同的好友间那些彼此不同、甚至互不相容的世界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忽然对圣训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每每奔往书店,总在圣训学类书籍的柜台前流连不休,细细地读着书脊上的每一行字,一旦发现与自己目前的知识储备相关的书籍,便毫不犹豫的买上。渐渐地,读得多了,买得也多了。
前一篇文章发出之后,收到了两篇回应。虽然内容不尽如人意,但至少说明我们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。
今日,听到一位著名阿訇的演讲,他在探讨国内一些较为敏感的法学问题,恕我愚笨,无法明晓他提出的一些奇异观点的意义所在,但我仍然捍卫他的辩驳和宣扬他认为的真理的自由,因而没有什么理由去说他。
上一篇,主要讲述了法学家们围绕圣训而产生分歧的第一个因素,即“什么情况下圣训才可以被遵循。”
而今天的内容,算是圣训VS法学系列的番外篇,作者在这一章中,详细地探讨了长久以来萦绕在人们脑际的一个疑问——法学家们所说的:
إذا صح الحديث فهو مذهبي
“如果圣训正确,那就是我的主张。”
我想推荐这部著作想了有半年那么久,然而始终未能下手。这个斋月,赋闲在家,写这篇文章的冲动于是更甚了,我甚至几乎下定决心要在斋月伊始建立一个群,在群里开讲这本著作。因为我私自觉得,国内的学者和群众太需要这样一部著作了。
然而始终好像有什么鬼影一般的障碍,使得所谓决心终究化为哀叹。斋月已近尾声,我于今夜,终于犹豫着下笔。托靠真主。
圣训学发展到今日,早已是硕果累累,然而直到今日,我们尚还停留于浅薄的扫盲期,往往因为不晓得术语的含义,而出现各种啼笑皆非的判断。
要么,判假成真,要么,判真成假,而更多的,是对真假之间太多不确定种类的盲目归类与判断。
对于健全、优良、羸弱等这些时常流传于人们口中的圣训学术语,我们的认知实在太过于简单粗暴。我们在事先不了解术语定义的情况下,各种术语汹涌而至,于是,在各种因素的渲染下,健全圣训往往被上升到了断然的级别,而羸弱圣训则被视为洪水猛兽,直接与伪造圣训相提并论。